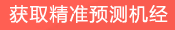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,母亲的话还是相当高屋建瓴、高瞻远瞩、高……高度了解她这个儿子的。她所担心的事毫不夸张的被她儿子的留学生活给验证了。当初她苦口婆心的叮嘱儿子一定要先把语言关给过了,别在学语言上浪费太多钱和时间。她儿子满脑瓜子自信的说:“不就是学说话嘛!”后来的事实说明澳洲人民对我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,在这点上,澳洲人民绝不次于我的任何一个老师。其结果就是通过4次IELTS、2次CULT,终于让我认识到,这年头话不是那么好说的。
不过巧合的是,另一个女生也的经历和我的也差不多,也学了一年的语言。不同的是,毕竟女生脸皮薄些,她只参加了1次IELTS和半次CULT。当中介公司的车把我送到homestay三个小时以后,我就认识这个女生——Jessie。两年半以后的今天,此时,她和我并肩坐在悉尼OperaHouse前的广场的护栏上,脚搭着翘的石沿,下面呜咽着的海水从我们坐下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它对我们的驱赶。她把头放在我肩上,海风经过我衣衫,不知道到达她身体时是不是已经有了我的体温。
“海风太硬了,我们走吧。”我说
“再呆一会。”……
“Leo,我们结婚吧?”
按理说,无论什么情况下,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说出这句话时,多少都会使人震撼一下。可我没有。这几个月来,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她说这句话了。我掏出根烟,紧接着又拿出打火机,然后又揣了回去。我从来不在和她这么近的距离的情况下抽烟。她的神态和她刚刚说话时的样子没任何变化。眼睛还在看着北岸那一小撮华丽的灯火,胖乎乎的脸蛋再依次泛起红晕,她的表情从整体上看就是——无表情。这让我很是失望,就如同刚到悉尼是过的第一个中国新年时有过的失望一样。
那天对于悉尼来说也只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罢了。可是留学生各个早就按捺不住了。当时我在wollongang的语言学校念IELTS班,说起这个我就来气,刚刚到时入学考试完事后老师问读哪个班,那阵我根本不知道还有直升班这一说。她给我列出的几个选择里,我就知道IELTS是怎么回事,而且据说这是语言班里最高的级别了。我理所当然的选了这个,当时还好一阵子自豪。后来到MQ的语言学校,我连IELTS班都没混上。
过年的那天下午,学校里稀稀拉拉的已经看不到几个人影了。晃晃荡荡的全是些什么黎巴嫩、印度的学生。本来wollonggang语言学校的主力就是中国人,其中还有近1/3的东北的,赶上过年哪还能有什么学生。中午遇到Edison,他是我的flatmate,我说让他到chinatown买点饺子,Jessie她们晚上可能会来。他哼唧着答应一声就走了。结果还没等我第一节课上完他就给我打电话说chinatown的饺子都卖完了,让我再去看看。我说你想什么呢,你去都没有,等我去还能有个屁啊,你到底去没去啊?他没吭声,我说算了,你到家附近的超市看看有没有,顺便在买点菜,回去我给你钱。